美国智库的组织结构及运作 —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
作者 陈怀临 | 2014-06-18 16:40 | 类型 行业动感 | 2条用户评论 »
美国智库的组织结构及运作 —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 周 琪 智库一般是指那些非营利性的、非党派的、独立于政府的、从事国内或外交政策问题研究的组织。当今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有时是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将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来剖析美国智库的组织结构、管理、运作方式、研究项目的设定及资金来源,并从中管窥美国智库的一些一般特征。 智库的定义及美国的主要智库 今天我们称之为“智库”(think tank)的组织最早诞生于美国,以后才逐渐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智库已经存在了100年左右,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政府研究所成立于1916年,胡佛研究所成立于1919年,外交关系委员会则诞生于1921年。 世界上的智库千差万别,学者们对之亦有不同的定义。然而近年来,人们提到智库时一般是指那些非营利性的、非党派的(但并不一定是非意识形态的)、独立于政府的、从事国内或外交政策问题研究的组织。①智库在组织规模、资金来源、研究专长方面有很大差异,除了上述共同点之外,它们在另一点上也是相同的,即都试图影响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 根据《2010年全球智库排名》(Global Go-To Think Tank Rankings)的统计,世界上存在着6300多个智库,它们分散在169个国家,其中1815个是美国的智库,而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智库有393个。②根据对智库成员、学者和记者的调查做出的智库排名,在世界最著名的25个智库中,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名列前茅。以下列出了美国排名前10位的智库名单: 第一,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这是一个注重科研和教育的组织,从事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其他主要智库相比,带有更多的学术特征,多年来一直名列美国最有影响的智库之首;第二,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该组织的研究专项是美国外交政策,它在华盛顿和纽约市都设有办公室;第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它致力于推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并积极促进美国参与国际事务。该组织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同时在莫斯科、北京、贝鲁特和布鲁塞尔都设有办公室,表明了其对俄罗斯、中国、中东、北约和欧盟研究的重视;第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这是一个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与军方关系较密切,它致力于对政府、国际组织、私人部门和市民社会方面的分析及对它们的影响;第五,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这是一个全球性组织,关注于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医疗、教育、国家安全、国际事务、法律、商业以及环境。兰德公司的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桑塔莫妮卡市,其办公室遍及世界各地。它在华盛顿周边的办公室设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市;第六,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该基金会从事各种问题的研究,包括国内和经济问题、外交和安全问题、法律和司法问题等;第七,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该研究所致力于加强企业自由,从事对政府、政策、经济和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第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该研究所就范围广泛的政策问题从事独立研究;第九,皮尔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该研究所致力于国际经济政策的研究;第十,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该机构的研究集中在公共政策上,诸如能源、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和经济机会、移民、教育和医疗照顾等。③ 美国智库影响公共政策的途径和方法 美国的智库,无论是保守派的还是自由派的,影响美国公共政策的途径和方法都是相似的。综合起来,它们主要采取以下方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在公共政策上的决策。 通过研究和发表研究成果来影响政府决策。智库通过出版著作、期刊、研究报告和简报等方式来阐述观点和提出政策建议。通过这些出版物,智库有时可以影响美国决策者的外交政策理念,有时则可以影响政府在具体政策上的选择。对政府实际政策影响比较大的是研究报告,这里可以举两个较近的例子。 一个例子是,2006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跨党派的“巧权力委员会”,由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L. Armitage)和软权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领衔。委员会于2007年11月发表了一份报告,要求美国政府制定更为全面的大战略,将硬权力和软权力结合起来形成巧权力,即在用武力打击美国敌人的同时,通过威慑、劝说和吸引来减少敌人的数量,以此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④这一观念被奥巴马总统所采纳,他在竞选中和竞选获胜之后,都表示他的政府将摈弃小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并主张在美国领导世界时,不仅要运用硬权力,而且还应更加重视运用软权力。 另一个例子是,在奥巴马当选为总统之后,在美国国内外的外交政策圈中出现了一批要求新政府重新思考美国在亚太地位的政策分析报告,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新安全中心”的合伙创始人、后来担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柯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人在2008年6月发表了题为《平衡权力:美国在亚洲》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虽然美国也在亚洲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成就,加强了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与中国和印度进行了更多的建设性交往,但是这些战术性的成果并没有集合成为一个成功的全面战略。美国的战略由于偏重于伊拉克和阿富汗而削弱了其向亚太地区进行重大权力转移的能力,这对美国传统上在这一地区平衡权力的作用构成了很大的挑战。”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的奥巴马政府开始认真地重新思考美国的亚太战略,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做出亚太政策的调整和“战略再平衡”与这些智库的分析报告有密切关系。 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在国会委员会审查立法的听证会上,除政府官员、利益集团的代表外,智库学者也常常被邀请在听证会上作证,这不仅为他们获得了影响国会立法的机会,还可以通过国会记录受到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而扩大他们的影响。 举行各种会议。所有的智库都会经常就国内外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举行对公众开放的论坛、研讨会、新书发布会、纪念会等,以此来同政府官员、同行、媒体和公众进行交流和互动。例如2011年秋冬在威尔逊中心举行了一场智库人士之间关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辩论,辩论的主题是“美国是否应抛弃台湾”。这场辩论是由一篇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引发的,该文章建议停止对台湾出售武器,理由是,台湾问题是可能在中美之间引起战争的唯一原因。此外,台湾问题阻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造成了中美之间的相互猜疑。而同中国建立起互信,有助于解决美国同中国在海洋安全、核安全、网络安全和太空安全方面的分歧。同时,作者一再强调,停止对台售武并不意味着美国抛弃台湾。虽然这场争论最终并没能改变美国对台军售政策,但它在美国政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 对政府官员进行培训。许多重要智库都设有对政府官员进行培训的项目,例如兰德公司、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都有对国务院官员的培训项目,大西洋理事会则设有对国防部高级军官的培训项目。 与媒体的互动。媒体是智库学者传播自己观点、影响公众讨论,从而间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重要途径。因此智库学者非常重视同记者建立联系,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布鲁金斯学会—案例研究 鉴于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会之一,而且其影响力位于全球和美国之首。下面就以它为例,来说明美国智库的组织结构、管理、运作方式以及资金来源。虽然诚如前文所说,不同智库在各个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对布鲁金斯学会的剖析中窥见美国智库的一些一般特征。 布鲁金斯学会的成立和发展。布鲁金斯学会主要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它的前身是1916年创建的政府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其使命是成为“第一个致力于在全国层面上分析公共政策问题的组织”。该组织的创建者慈善家罗伯特·S·布鲁金斯(Robert S. Brookings)(1850~1932)还曾资助成立了其他两个组织—经济研究所和圣路易斯市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这三个机构于1927年12月8日合并成为布鲁金斯学会。 其第一任总裁为哈罗德·莫尔顿(Harold Moulton)。在大萧条期间,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发起了大规模的研究来解释大萧条的基本原因。哈罗德·莫尔顿和其他经济学家在罗斯福新政时期领导了反对新政政策的努力,因为他们认为新政措施阻碍了经济复苏。1941年当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转向支持政府。1948年,布鲁金斯学会被政府要求起草一份有关如何管理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的建议。从1952年其第二任总裁罗伯特·卡尔金斯(Robert Calkins)继任起,布鲁金斯学会开始从事政策研究。卡尔金斯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获得了对布鲁金斯学会有保障的资助,并围绕着经济研究、政府研究和外交政策项目重组了学会。1957年该学会迁址于其现在华盛顿的所在地。 历史上,布鲁金斯学会为美国制定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国会预算办公室做出了贡献,并对解除规章、税收改革、福利改革和对外援助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的构成和管理。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作为非营利组织,它必须严格遵守美国税法501(C)(3)条款的有关规定。布鲁金斯学会的最高决策层是董事会。当前的董事会共有83名成员,⑥他们都是著名的企业家、银行家和学者。 布鲁金斯学会的日常运行遵循企业管理的方法,由总裁负责。总裁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首席执行官,负责推荐研究项目,批准出版,挑选研究员。有三个机构支持他的工作,它们是行政办公室、总顾问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 在总裁之下,学会的构成分为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两大部分,行政管理部分由5个部门组成,即财务部、运营部、联络部、发展部和出版社,它们分别对资金、后勤服务、媒体服务、人事与培训以及出版社进行管理。每一个部门由一名副总裁掌管,他兼任该部门的总监或主任,并直接对总裁负责。 研究部分根据研究领域划分为五个部门,分别是:外交政策、全球经济与发展、经济政策、城市政策、治理研究。每一个部门也由一名副总裁主管,并下设若干个研究中心。具体而言: 一、外交研究部下设:塞班中东政策研究中心(包括设在多哈中心的)、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包括设在北京的中心)、美国和欧洲研究中心、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外国境内流离失所者项目、拉美倡议、21世纪安全与情报中心。外交政策部是布鲁金斯学会中获得预算最多的研究部; 二、全球经济与发展部下设:发展援助与治理倡议、拉美经济与社会政策倡议、非洲增长计划、统一教育中心; 三、经济研究部下设:英格堡医疗照顾改革中心、儿童与家庭中心、社会动态与政策中心、退休保障项目、布鲁金斯城市税收政策中心、汉密尔顿项目、商业、政府和创新倡议; 四、城市政策部下设:大华盛顿地区研究计划; 五、治理研究部下设:布朗教育政策中心、技术创新中心、行政教育中心。⑦从以下布鲁金斯学会组织结构示意图可以看出,国际研究是布鲁金斯学会最大的研究领域,也是近年来扩大最快的领域。 整个布鲁金斯学会是围绕着研究而运转的,其他非学术研究部门都是为研究服务,因研究而存在。对于布鲁金斯学会而言,研究成果的高质量是整个学会的生命,布鲁金斯学会的生存和发展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布鲁金斯学会标榜自己的使命是“提供有创新的、实际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三个广泛目标:加强美国的民主;为所有的美国人创造经济和社会福利、安全和机会;确保一个更开放、安全、繁荣和合作的国际体系。”此外,“布鲁金斯学会及其学者在其研究中并不关心如何影响国家的意识形态方向,而是倾向于聘用拥有强有力学术地位的研究者”。⑧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2013年的年度报告,学会的总人数为270人,包括居住在美国或国外的人员。⑨研究人员共有100多名,他们的头衔是资深研究员或研究员,其中有些是短期在美国从事布鲁金斯学会项目研究的客座研究员。其他人员都是管理人员或研究辅助人员,从事会务与设备管理、信息技术或图书馆服务等,他们支持了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对于整个学会的研究工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布鲁金斯学会中,同中国研究关系密切的两个中心是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和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下面着重对它们作一些介绍。 东亚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 Policy Studies)。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原名东北亚研究中心,它是布鲁金斯学会一个成立较早的中心,虽然它的活动非常引人注目,但它实际上仅有2名正式研究员,其中之一是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另一名是一个在墨西哥出生的日裔美国人,他主要从事日本经济、国际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研究。由于东亚政策研究中心能够从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得到大量资助,它有经费邀请许多访问学者(Visiting Fellow)到中心做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都属于该中心的研究成果。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曾受邀做研究的访问学者来自东亚的各个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越南、柬埔寨、蒙古、菲律宾、泰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省,甚至还包括俄罗斯。⑩在访问学者访问结束前夕,该中心将举行一次面向公众的研讨会,安排他们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做发言,并回答公众提出的问题。之后,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被刊登在学会的网站上。 东亚政策研究中心是不久前才从东北亚研究中心更名为现在的名称,这意味着其研究的地域范围将正式扩大到包括东南亚,虽然这是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与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有关,因为在美国对战略重心转移的同时,其在亚太地区内的战略重点也变为向东南亚地区倾斜,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项目也需要随之扩大。 从2014年起,由于经费有限,邀请访问学者的政策也将改变为基本上仅限于来自为中心提供资助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由于这一新的规定,中国学者可能会不再或很少能得到资助到布鲁金斯学会做研究,因为中国不是资金的捐赠国。 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已经发展成为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研究领域里仅次于萨班中东研究中心的第二大中心,后者的成员仅比前者多一人。它是前高盛集团的首席执政官约翰·桑顿捐巨资设立的。它最初成立时只有3名成员,目前扩大到8名,其中7名是在本部工作,1名是布鲁金斯学会设在清华大学的中心的主任。中国研究中心设主任和副主任各一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心的年度预算筹款和进行行政管理,而筹款是一项繁杂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像李侃如这样曾担任中心主任的知名学者辞去这一职务的原因,因他不愿为筹款而占用自己宝贵的研究时间。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副院长2012年访问布鲁金斯学会时同中国研究中心达成的协议意向和以后的正式协议,该中心也开始吸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资助的访问学者。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位来该中心做研究的访问学者已经开始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有很多都曾在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工作过,被称为“学术实践者”(Scholar Practitioner)。现任总裁斯特普·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就是一个典型,他是一名美国外交政策的专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其职业生涯跨越媒体、政界和学术界,其研究专长是欧洲、俄罗斯、南亚和核武器控制。塔尔博特曾担任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并撰写过多种著作,其最近的一部著作是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 像其他著名智库一样,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政府官员后备人才的蓄水池或储备库。许多官员在任期结束之后,会转到这里工作,一方面利用他们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经验和人脉关系来从事研究,另一方面,在此做“充电”,为今后有机会再度进入政府做好知识储备。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之间常见的“旋转门”现象。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举近期为例,杰弗里·贝德(Jaferey Bade)2002年从国务院退休之后,到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担任主任,在奥巴马竞选总统之时,他在人们普遍不看好奥巴马的情况下,选择支持他,成为他的亚洲和中国政策顾问,并在奥巴马当选之后于2009年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事务主任。两年之后,他离开白宫重返布鲁金斯学会任资深研究员。现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曾供职国会、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著名中国研究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曾是密执根大学的教授,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主任,待他重返学术界后不久,选择了在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工作,曾担任过中心主任。 据统计,到2013年,布鲁金斯学会先后进入奥巴马政府任职的有30多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担任第二届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苏珊·赖斯(Susan Rise)和2009年被任命为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的彼得·奥斯泽格(Peter Orszag),后者在2001~2007年期间曾在布鲁金斯学会任资深研究员,并担任经济研究部下的汉密尔顿项目的第一任主任,2007年出任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 “质量、独立、影响”。布鲁金斯学会的信条或者说是自我“训诫”是“质量、独立、影响”。这一要求在各种场合被反复提及,也是布鲁金斯学会为之骄傲和自我标榜之处。 质量。布鲁金斯学会要求其学者进行高质量的、独立的研究,并提出有创新性的实际政策建议。布鲁金斯学会自信,“在成立后的90多年中,它为决策者和媒体提供了有关广泛的公共政策的高质量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其学者对当前的、正在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美国和国际上提出了与这些问题有关的新思想。”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不仅从事政策研究,也进行学术研究。他们大都毕业于名牌大学,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发表在学术期刊中,也可以发表在布鲁金斯学会自己的网站中。但是,除了日常的政策分析和学术活动之外,他们不间断地从事的一项工作就是撰写专著,可以说专著是他们在政策界和学术界立足的根基。他们平时的研究也都是在为撰写专著做积累。例如,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专著:《未知的海峡 两岸关系的未来》,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成也在2013年发表了新著《中国烟草的政治版图》。每隔两、三年,学会的学者们都要发表自己的一本专著,作为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结晶和总结。布鲁金斯学会有自己的出版社,每年出版20~30本专著,学会大楼内设有自己的书店,出售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大楼内的走廊里展示着学会研究员的新著。这些都显示了作为一个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对学术研究和专著之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在约翰·桑顿中心的努力下,布鲁金斯学会近年来还翻译出版了中国作者撰写的系列丛书。 独立。“独立”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三个信条中可能是被视为最重要的信条。布鲁金斯学会标榜自己通过各种途径发表研究成果,是为了引起或有助于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但其研究不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也不能向公众提出政治议程。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的独立性通过以下措施来保证: 第一,资金捐助者不能干预研究题目和研究结论。布鲁金斯学会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基金会、公司和个人的捐款,以及一些出版物收入和其他投资收入。学会把筹到的资金用于研究和教育活动。这些捐助者不能对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项目和研究结论进行干预。虽然布鲁金斯学会也进行少量的非保密的与政府签合同的研究,但它保留发表这些成果的权利。 第二,非党派性。为了保护布鲁金斯学会执行非党派的政策,学会成员必须遵守以下与政治活动有关的规定:他们可以在非党派的和不排除其他观点的基础上为政府官员和公职候选人提供有关公共政策的分析和建议。但如果学会成员是为候选人的竞选或政治组织提供建议,如政治行动委员会或政党竞选委员会,他们就必须使用工作以外的时间,而且必须表明他们的行动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不代表布鲁金斯学会。他们在公共场合或媒体采访中不能为候选人代言,也不能在竞选中或同候选人的交往中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设备或其他资源,包括助手的时间、电子邮箱帐户、计算机和电话,或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场地举行政治活动。如果研究人员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他们就必须离职。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虽然有许多布鲁金斯学会的成员支持奥巴马并帮助他竞选,但他们都严格遵守了上述规定。 第三,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都进行独立研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选择研究课题,其对时间的支配也有很大的灵活性。研究人员的观点都仅仅代表个人,而不是布鲁金斯学会、其董事会成员或管理人员。 需要说明的是,进行独立研究和学会成员不以学会名义参与政治并不妨碍布鲁金斯学会或其研究员自己的政治倾向。一般来说,与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相比,布鲁金斯学会被认为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智库。然而,从历史上看,该学会的思想倾向与学会领导人所持立场有密切关系。随着1932年学会创始人布鲁金斯的去世,学会发生了明显的右转,对罗斯福新政多有批评。肯尼迪担任总统之后,学会的研究人员参加了制定“新边疆”构想的特别工作小组,在从空间研究计划到经济政策等方面为肯尼迪政府出谋划策。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当肯密特·戈登(Kemnit Gordon)担任学会总裁时,学会的政治倾向回摆向自由主义,帮助约翰逊政府拟定了“伟大社会”计划,支持建立大政府,但同时反对越战。戈登离任后,学会的思想倾向再次右转。1995~2000年担任学会总裁的迈克尔·阿马克斯特(Machael Amacost)1977~1978年曾在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亚洲和中东事务,1984~1989年又在里根政府下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并在老布什政府下担任驻日大使,可以说是与共和党的关系更密切。现任总裁塔尔博特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在他的领导下,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更为接近。 布鲁金斯学会声称其研究员“代表了不同的观点”,并把自己视为“非党派”的智库,而媒体常常把布鲁金斯学会描述为“自由-中间”派,或“中间派”。对国会1993~2002年记录的一项学术分析发现,保守的政治家引述布鲁金斯学会的频繁程度不亚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它在1~100的政治光谱的得分中(1代表最具保守主义倾向的,100代表最具自由主义倾向的)得到了53.3分,显示了其整体政治倾向是中间略偏左。 影响。布鲁金斯学会因其严谨的研究和各种活动获得了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影响力。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2012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Report),布鲁金斯学会被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它还被《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年度智库索引”列为美国排名第一的智库。在200个最有影响的美国智库中,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受到媒体最广泛的引证,也是政治家最经常引证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一般与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起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政策研究机构。 布鲁金斯学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建立其影响力。学者经常向记者提供评论、分析和背景信息,出现在电视或广播节目中;时常在国会作证;向决策者及其在重要问题上的助手作情况简介。学会经常就国际事务中的热点、重点问题举办向公众开放的研讨会,邀请一些专家做主题发言,之后回答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学会还会举行新书发布会,除请作者介绍自己新著的主要内容之外,还会请专家作评论。学会的学者也经常接待各国来访的官员或学者,与之交换观点,或交流重要信息。学会的教育部门每年设立一些对美国各级官员的短期培训项目,培训内容涉及美国政治的各个方面。例如2012年曾举行为期三天的“美国安全政策与决策体制”培训,学员大都来自情报部门、国防部和国务院,由美国安全政策的专家、前政府高级官员和议员为他们做讲座。 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年度报告。学会的出版社出版学会研究者以及学会之外作者的著作和杂志,包括《布鲁金斯学会经济活动论文》(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此外,布鲁金斯学会有一个庞大的信息技术部,其成员为传播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成果和扩大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站展示了学会学者的各种成果,从论文、报告、评论、会议发言到新书简介,无所不包,而且可以免费下载。普通公众如果注册为会员,就可以经常获得学会举办活动的信息,并可注册参加由它举办的各种向公众开放的活动。 表1: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重点和发挥影响的方式 布鲁金斯学会的经费来源与开支 根据2013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年度报告,布鲁金斯学会的经费来自基金会、公司和个人,也有少量来自政府部门。 表2:布鲁金斯学会2013年经费来源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Brookings Annual Report 2013, pp. 35~37绘制。 在捐款者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们所熟悉的基金会和公司等。在捐款10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者中,基金会有福特基金会、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公司有摩根大通公司、微软公司;国家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个人有约翰·桑顿。 在50~99.9999万美元捐款者的名单中有美利坚银行、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 在25~49.9999万美元的捐款者中有AT&T公司、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日本基金会全球伙伴中心、日本国际合作署、韩国基金会、挪威政府、瑞士政府、台北驻美国经济与文化代表处、美国国际开发署。 在2.5~4.9999万美元的捐款者中包括美国运通公司、威瑞森通信公司(Verizon Communication),以及美国能源署。 在1~2.4999万美元的捐款者中有欧洲投资银行和欧盟。捐款在10万元以上的基本都是基金会、公司和政府机构,而捐款在1万美元以下的全部都是个人。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2013年年度报告,学会的资产为4.6亿美元,其中净资产为40423.3万美元,负债为5841万美元,总资产和负债为4626.43万美元。 表3:布鲁金斯学会的资产构成(2013和2012年比较)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 Brookings Annual Report 2013, p. 39. 表4:用于学会运转的资金(2013和2012年比较)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Brookings Annual Report 2013, p. 38. 在2013年的总收入中,赠款占 84%,出版收入占2%,捐款占11%,杂项占3%。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运行开支中,2013年用于项目研究的经费为6904万美元,其中用于外交政策研究的费用为1992.6万美元,占总研究经费的29%;第二大项目开支是经济研究,经费为1474万美元,占总项目开支的21%。此外,从上表中可以发现,虽然与2012年相比,2013年布鲁金斯学会的总资产增加了2571.2万美元,但其用于总运营的收入从2012年的13203.7万美元减少到9785万美元,减少了26%以上。减少的最大部分是赠款、捐款和合同经费,仅这一项就比上一年减少了3456万美元。 表5:2013年布鲁金斯学会项目开支数额(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Brookings Annual Report 2013, pp. 38~39提供的数据绘制。 从对布鲁金斯学会2013和2012年的财政情况的比较分析中也可以看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许多美国智库面临着筹款困难时,连布鲁金斯学会这样运营良好的一流智库也不能完全幸免。可见,今后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智库的兴盛和发展还将极大地依赖于美国经济走向好转。
【注释】 ①Donald Abelson: ”Think Tanks - Definition, Their Influence and US Foreign Policy,”. ②③Rachel Cooper, ”Think Tanks - What is a Think Tank? Organizations Shaping ④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Jr.,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A Smarter, ⑤Kurt M. Campbell, Nirav Patel and Vikram J. Singh, The Power of Balance: America in iAsia, ⑥根据布鲁金斯网站,http://www.brookings.edu/about/leadership/trustees. ⑦以上对布鲁金斯学会组织结构的介绍来自学会内部分发给每个工作人员的示意图。 ⑧布鲁金斯学会网页,http://www.brookings.edu/about#research-programs/. ⑨Brookings Annual Report 2013, p. 1. ⑩根据2013年12月8日对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的访谈。 布鲁金斯网站,http://www.brookings.edu/about#research-programs/ Brookings Annual Report 2013, p. 1. Neil A. Lewis, “Silicon Valley’s New Think Tank Stakes Out ‘Radical Center, ‘”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5, 1999 Tim Groseclose and Jeffrey Milyo, “A Measure of Media Bia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CXX, Issue 4 (November 2005), p. 1200。 | |
雁过留声
“美国智库的组织结构及运作 —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有2个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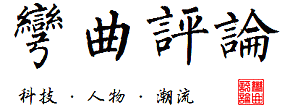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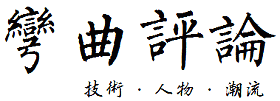

 (2个打分, 平均:4.50 / 5)
(2个打分, 平均:4.50 / 5)
是为了呼应彻查社科院吗?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给所谓强调无党派性迷惑了,无党派性不代表无国家性,作为米国意识形态(如米国自认的民主、自由等)的推广者,这些协会本身就是天佑米国意识形态的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