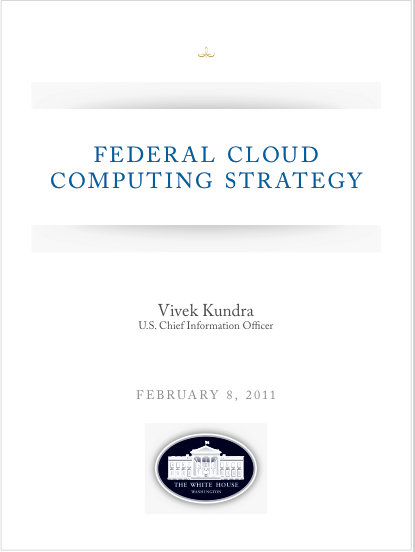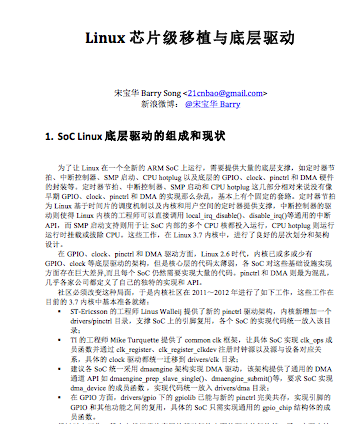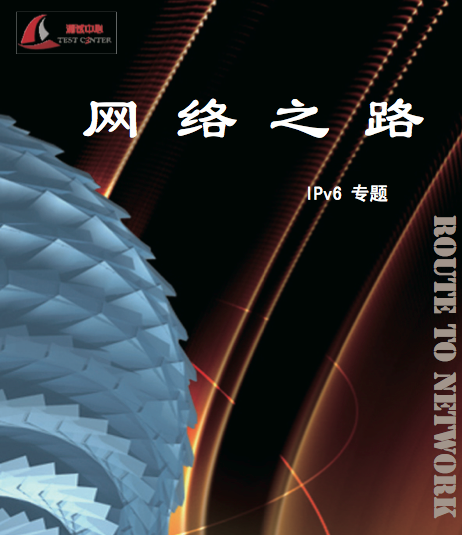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华为和中兴公司的调查报告(全)
作者 陈怀临 | 2013-04-20 09:16 | 类型 弯曲推荐, 科学与中国, 行业动感 | 7条用户评论 »
美国联邦政府的云计算战略-Cloud First Policy
作者 陈怀临 | 2013-03-22 18:32 | 类型 云计算, 弯曲推荐, 数据中心 | Comments Off
王齐 。《后科技年代--操作系统的思考》
作者 陈怀临 | 2013-03-14 21:22 | 类型 弯曲推荐, 操作系统 | 35条用户评论 »
|
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这是智慧的岁月,这是愚钝的岁月;这是信仰的时刻,这是怀疑的时刻;这是光明的瞬间,这是黑暗的瞬间;这是希望的春季,这是失望的冬季;我们无所不有,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步入天堂,我们直下地狱…
自有文字记载开始,历史向前推进了五千余年。在这段并不算漫长的时间里,生活在今天的人类是幸运的。我们的祖先没有像今天这样容易地获取食物,在遥远的彼岸,美国用3%的农业人口养活了97%的非农业人口;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帝王将相没有像今天的普通人这样容易地获得信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汗牛塞屋的图书馆模式成为过去;国家的边界没有像今天这样模糊,公司的崛起在不断跨越着时间与空间;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没有像今天这样模糊。我们处在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之中。 这场盛世源于硅的出现。每在回味硅工业的发展历程,我总在质疑这段历史的真实性。硅工业的诞生是一段传奇,这一传奇超越了人类历经五千年农业与工业积累而后的想象。很多人在质疑究竟是人还是神发现了硅。这些质疑无法改变硅工业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巨大影响,我们现今世界的一切几乎都与硅有关。硅工业的不断演化加快了世间万物的新旧更迭。在硅工业持续发展的60余年时间里,世间万物的产生,发展,消亡,过于匆忙,一个时代尚未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已在我们不及回味中跃上舞台。我们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乱世之中。 硅工业在持续改变其他行业的过程中,改变了自身。硅工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硅晶体管的诞生到集成电路的出现;摩尔定律持续正确那段只属于硅工业的,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如今的后摩尔时代。在第二段时间里,硅工业迅猛发展,Intel在此时发展壮大。准确地讲,只有在这段时间,Intel才是Intel,天下之士可以仅凭使命加入这家公司,投入这场令人热血沸腾的,只属于硅的时代。 硅工业至今依然在进步,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如同人类历史上其他伟大发明,硅工业正在逐步退去光环。硅工业不是不再重要,而是渗透到了人类所能触及的每一个领域,正式成为传统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Intel在近期或是将来推出再多的Tick,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硅工业正在逐步失去前进的动力。 硅的举步维艰并不会使其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而是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硅。基于硅的各种设备将继续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度,如食物衣服般同等重要。但是我们有谁能知道身上衣,口中食出自哪个农民之手。如今的硅工业已经重要得让越来越多的人忘记了他的重要性。硅工业的这一现状将对其几个最重要的分支带来直接的影响,处理器和附着在处理器之上的传统操作系统,和一切与此相关的,曾经辉煌的生态环境。 我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如嗜血般关注处理器微架构,这个行业依然波澜不惊,偶尔冷静思考这门学科的未来,却再也难以找到在这个领域投入更多时间的理由。在工程界,即便是在理论界,已没有什么可以令热血为之沸腾的发现。偶尔看些论文,无论是曾经Most Influential的经典,或是近期出现的一些说法,从中看到的不过是一些近亲繁殖的影子。 处理器微架构, x86还是ARM,采用什么样的集成策略,究竟使用什么工艺都已不再重要。从最近的这段时间看,在传统的PC领域,x86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在手持终端领域,ARM占尽先机。如果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在可以预期的3到5年之内,如果Intel没有做出重大且激进的变革,将逐步远离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公司行列。 ARM在手持移动领域的领先并不意味着这个阵营的伟大,而是x86阵营打败了自己。念及这段即将别离的往事,心中所思所想的是6500万年前白垩纪恐龙的灭绝。在处理器微架构领域,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留出更多的空间去继续容纳着庞然大物。ARM可以化整为零,活得稍好些。从更长远的角度上看,x86与ARM间没有赢家。x86与ARM之争对参与的双方依然重要,却偏离了这个时代的主战场。这个时代不再属于硅与处理器微架构,依托在处理器微架构之上的传统操作系统也已是昨日黄花。 在1975年,比尔盖兹也许未曾设想他一手创建的公司,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垄断着桌面操作系统的一切。这种垄断,经过无限放大后,使微软可以涉及与桌面软件相关的任何领域。当时的微软没有任何实质性对手。微软的前行,伴随着众多公司的倒塌。这家公司在最强大的时候,甚至可以采用“模仿你,不行就和你比流血,再不行就挖光你的人”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段。通过与Intel事实上的联姻,组成的PC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向无敌。因为这种无敌所产生的自信,使得微软并没有真正重视周边环境的变化。 | |
宋宝华 。《Linux芯片级移植与底层驱动》
作者 陈怀临 | 2013-02-17 10:52 | 类型 弯曲推荐, 操作系统, 科技普及 | 1条用户评论 »
Linux文件系统演进研究 FAST’13最佳论文
作者 blakegao | 2013-02-16 13:28 | 类型 学术园地, 弯曲推荐 | Comments Off
H3C . 《网络之路》(5)-IPV6专题
作者 陈怀临 | 2013-02-03 07:11 | 类型 弯曲推荐, 科技普及 | Comments Off
香港应科院多核软件平台团队诚聘
作者 fastgateteam | 2012-11-13 06:51 | 类型 工作机会, 弯曲推荐, 行业动感 | 15条用户评论 »
|
首席好,弯曲的各位前辈,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你们好。 我们来自香港应科院(www.astri.org)多核网络协议栈软件团队。是一群热爱系统设计的大宋子民,所在的项目组专注于多核处理器下的快速包处理的软件平台研发,项目介绍可参见下面的链接。 More information about FastGate 目前团队因业务拓展急需优质工程师的加盟。工作职责包括软件平台、功能模块开发,维护与测试。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您不必面面俱到,但您至少能一剑封喉): 良好的C语言编程能力; 较强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基础; 熟悉Linux或其他网络协议栈架构; 网络协议相关开发经验; 防火墙相关开发经验; WLAN/LTE相关开发经验; Linux内核/模块开发经历; Cavium SDK或Intel DPDK; 多核软件开发及性能优化经验。 弯曲在陈首席多年的苦心经营下已成藏龙卧虎之地,如果您跟我们一样对系统设计、软件开发依然保持着理想、激情和执著,那就联系我们吧! 工作地点: 香港 简历投递: allenlu@astri.org QQ: 37692792 MSN: lvjc@163.com | |
包云岗 。普林斯顿 。《世纪图灵纪念》
作者 陈怀临 | 2012-11-02 13:58 | 类型 人物评述, 学术园地, 弯曲推荐, 计算的美丽 | 10条用户评论 »
|
[编者注: This article is published on behalf of the author of Dr Yungang Bao。] 1912年“计算机科学之父”阿伦•图灵(Alan Turing)诞生。1930年代,计算机先驱们齐聚普林斯顿小镇,图灵、邱奇(Alonzo Church)、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哥德尔(Kurt Gödel)、克林(Stephen Kleene)……。 2012年,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世纪图灵纪念庆典”,邀请了20位嘉宾(包括8位图灵奖得主)介绍计算机科学的前世今生。 1. 图灵机的偶然与必然 邱奇在1930年代初提出λ算子,核心思想是“万物皆可为函数”。邱奇给出一组无类型(untyped)的函数定义规则(因为无类型而无法区分函数与参数,所以λ算子会产生递归),然后又加了几条规则,试图用函数来形式化整个逻辑系统。但后来他的学生克林发现这套逻辑系统不一致。邱奇非常失望,把整个逻辑部分全都抛掉,在1935年只把λ算子部分发表了。所以,λ算子对邱奇本人来说是一段很痛苦的经历,再也不想向其他人提及。斯科特教授说,他在普林斯顿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导师谈过λ算子。 1936年5月,图灵也发表了著名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提出了图灵机。随后图灵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跟邱奇读博士。这段时间,他又证明了图灵机和λ算子也是等价的。而在1936年前后,克林提出了一般递归函数(General Recursive Functions),后来邱奇证明和λ算子也是等价的。因此,图灵机、λ算子和一般递归函数都是等价的。 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冯诺伊曼在了解了图灵的工作后立刻意识到其重要性,他极力邀请图灵博士毕业后继续留在普林斯顿工作,但图灵非常想家,还是婉言拒绝了。随后1945年,在距离普林斯顿不远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诞生了。但它太难操作了,人们开始寻找高效的编程方式。于是从195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设计高级语言。1957年,巴克斯(John Backus)带领团队率先发明了第一个高级语言Fortran。与此同时,麦卡锡(John McCathy)则受λ算子启发,在1958年设计出了LISP语言。邱奇肯定不曾想过,曾经因为逻辑不一致而几乎被他抛弃的λ算子成了计算机高级语言的基础。 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巧合。在1936年以前的几千年人类文明中,人们从来没有思考过“什么是可计算的”这个问题,但在1935~1936年的一年间,却一下子提出了三种等价的理论,这岂不是太巧合了?紧随斯科特教授,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沃德尔(Philip Wadler)教授在第二个报告《邱奇的巧合》( Church’s Coincidences)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事实上,人类科技史中诸如此类的巧合比比皆是,沃德尔教授又举了好几个例子。比如,牛顿在1666年发明了微积分,而莱布尼茨在1675年也独立发明了微积分;达尔文在1859年提出进化论,而华莱士(Alfred Wallace)其实在1855年也提出了相同的理论;而贝尔和格雷(Elisha Gray)在神奇地在1876年的同一天提交了电话发明专利。 表面上历史充满了各种巧合,但如果把这些巧合放回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出现又是必然的。今天我们将它们视为巧合是因为后人割裂了历史,只记住了少许闪光点而忽略了知识变迁过程中的幕后推手。 为了揭示图灵机巧合的必然性,沃德尔教授向听众还原了计算理论变迁的那段辉煌的历史。故事要回溯到1900年希尔伯特提出的23个数学问题,其中第2个问题是能否机械化地证明算术公理系统的一致性。1928年,希尔伯特又进一步提出了判定问题(Entscheidungsproblem),即能否找到一个算法自动地判定谓词(一阶)逻辑表达式是真还是假。1931年,哥德尔提出了不完备性定理,他构造了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是不可证明的”,对希尔伯特的第2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为了证明不完备定理,哥德尔写出了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哥德尔的程序只是用逻辑公式去形式化了几个步骤,并未定义编程规则)来验证一个命题是否能被证明。人们又从哥德尔的“程序”中觉察到希尔伯特判定问题也可能不存在答案,即没有这样的算法或不可计算。但要想证明这点,首要的是定义清楚什么是算法(或什么是有效可计算性,Effective Computability)。 全世界的数学家们都在思考可计算性定义问题,普林斯顿的数学家们也不例外。1932年,邱奇给出了第一个定义——λ算子,他本希望用λ算子来形式化逻辑系统。那时,克林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跟邱奇攻读博士学位,也在思考可计算性定义问题。当邱奇提出λ算子后,克林发现λ算子能表示整数算术系统,这似乎是可计算性的定义了。他和哥德尔讲了这个想法,但哥德尔并不认为这定义了可计算性。克林不服,向哥德尔下了战书——如果这个定义不对,那请把你的定义拿出来,我能证明两者是等价的。1934年,哥德尔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报告中提出了一般递归函数概念。当时,刚博士毕业的克林记下了笔记。两年后(1936年),克林将一般递归函数具体化,并证明了和他之前的定义是等价的。随后邱奇又证明一般递归函数和λ算子也是等价的,并用λ算子证明了希尔伯特判定问题是不可计算的。不过“狡黠”的哥德尔还不肯承认,狡辩道,也许我的定义是错误的。 1935年的英国剑桥大学,纽曼(Max Newman)教授正在给一个关于希尔伯特判定问题的报告。他总结道,现在解决判定问题的关键就是找到可计算性的定义。23岁的图灵也在报告现场,他便开始独自思考这个问题。1936年,他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用图灵机来定义可计算性(或算法),然后用图灵机重写了哥德尔在1931年的那个“程序”,也证明了希尔伯特判定问题是不可计算的。尽管图灵的证明方法比邱奇晚了几个月,但却更直观、更易于理解,而且更像一台可操作的机器。 在1936年前后的一年间提出三种完全等价的可计算性定义,都源自于希尔伯特的判定问题。到此,听众们恍然大悟又若有所思–这段经典的历史对我们又有何启发呢?我们又能在人类知识变迁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2. 大科学(Great Science) 什么是大科学?姚教授认为有两个参考标准:1)大科学是多学科交叉产生的;2)大科学伴随着颠覆性技术的出现。 姚教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X射线晶体学。1895年,伦琴发现X光;1912年冯-劳埃通过X衍射证明了X是波;1913年,布拉格父子提出用X射线来测晶体结构的方法;于是到了1920年代,人们开始用X射线来测金属、离子以及大分子的结构。随后人们开始讲X衍射技术应用到了生物领域,终于1950年代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开辟了生物研究新疆界。 另一个是计算机科学。二十世纪初,希尔伯特提出数学的机械化证明。1936年图灵机出现,但只是理论模型。1945年,电子计算机发明,随后肖克利等发明了晶体管,从此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便按照摩尔定律飞速发展,这是数学和半导体技术的结合。毫无疑问,这两个例子都是伟大的科学,它们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知识和生活。 回到姚教授的报告主题,他认为量子计算正是X射线晶体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结合,并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以西蒙问题(Simon’s Problem)为例,假设F(x)会将2个不同n位的0-1比特串x和s映射到同一个值,即F(x+s)=F(x),那么给定x,如何找到对应的s?传统的算法需要对F(x)进行2n次查询操作。量子计算则可以把F(x)和F(x+s)看做是两个晶体,然后用光线去照射,这样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干涉条纹,然后就可以得到s。这样的操作只需要3n个光子就可以,其中的原理和用X射线衍射结果反推出晶体结构很相似。另一方面,世界各个国家都在量子计算研究投入很大的经费,量子器件的发展速度也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例如,目前已经有技术能实现14个粒子的量子纠缠;现在已出现传输单个光子的技术,这就意味着可以利用单个光子发送量子信号。姚教授认为,虽然很多人对量子计算表示怀疑,但从事量子计算的科学家们却要乐观的多。 姚教授做研究遵循大科学的标准,过往的经历也使他更坚信做研究应该选择有价值的问题。姚教授2004年回清华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展研究工作,过去两年我很幸运有机会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博士后,所以这里的科研价值观,我也有些体会。在普林斯顿,很多教授和学生都非常自信,认为只要他们决定去做一件事,就一定能做好。另一方面大家又意识到,做一件琐屑的小事,所花的精力其实并不比有价值的大事少。因此,在这种自信心和价值观的支持下,他们就敢于去尝试一些很有挑战的问题,有时甚至会跨很大的方向。 李凯教授的研究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博士工作首次提出了软件分布式共享内存(Distributed Shared Memory,DSM)思想,到普林斯顿后又做了硬件共享内存系统SHRIMP,之后研究用多个投影仪组成可扩展显示墙(Scalable Diaplay Wall),后来又转到研究基于内容的多媒体搜索技术。而创办Data Domain公司时则进入存储领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数据冗余存储产品。如今,他和脑科学领域专家合作,开展脑科学计算的前沿研究。虽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像DSM和Data Domain那样成功,但通过开展这些有挑战的项目,积累了许多高质量论文(h-index为64),培养了不少出色的人才,也在同行中建立了学术威望。 3. “定义”的力量 机器学习并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所以了解并不多。但瓦伦特教授的报告充满了想象力,给我很多联想和启发。他认为图灵不仅仅是一位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更像是一位自然科学家,而计算机科学也可看作是一门自然科学。他在幻灯片上摘出了图灵1948年的论文《智能机器》(Intelligent Machinery)中一段话,“… genetical or evolutionary search by which a combination of genes is looked for, the criterion being survival value.”,然后说图灵所思考的已经超越了计算机科学,可以归到自然科学范畴了。报告中,他又说道其实机器学习的必要性和意义图灵早就在1948年就指出来了,许多听众感到有些茫然。只见瓦伦特教授翻到一页幻灯片,又摘出了图灵那篇《智能机器》 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有这么一句话“the learning of languages would be the most impressive”。瓦伦特教授稍加解读,众人顿时恍然大悟,不禁感慨图灵真如神一般高不可及,而学术大师们则像神父一样能读懂神的思想,向世人传达神的指示。 瓦伦特教授的报告中提到好几个有趣的定义,比如什么是学习,什么是进化。这些高度抽象的概念,瓦伦特教授却能用数学进行漂亮的形式化定义,令人叹为观止。很多难题无从下手时,正是因为问题没有定义清楚,而巧妙的定义经常另辟蹊径,帮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有个笑话从反面诠释了定义的能量。一位哲学教授将一把椅子提到讲台上,对学生们说,今天哲学课考试题目是–证明这把椅子不存在。学生们开始冥思苦想,但只过五分钟有位学生即交卷了。教授一看,答卷上只有五个字,但连声称绝,打了满分。这五个字是——"什么是椅子?" 这让我联想起在普林斯顿时与李凯教授的一次讨论。当时,我们希望对比两个程序行为是否相似,这听起来也是一个无从下手的问题。于是李凯教授让我先去定义“什么是程序行为?、“什么是相似?”当我把这些问题定义清楚后,解决思路就明确了。这次经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只有将问题定义的越清晰,才能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法。 如果说好的定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那伟大的定义往往开辟新的领域。这样的例子在计算机科学发展史上比比皆是。除了瓦伦特教授定义了什么是学习开创机器学习领域外,还有图灵用图灵机定义了什么是可计算,开创了整个计算科学领域;香农(Claude Shannon)通过不确定的概率定义了什么是信息,开创了信息论;里维斯特(Ron Rivest)等通过概率上的不可区分性(indistinguishability)定义了什么是安全,开创了计算机时代的安全领域。 4. 互联的未来 斯密特报告的主题是未来,他给现场听众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未来蓝图。未来智能手机将越来越便宜,如今已经有几十美元的Andriod手机了。未来的市场主要会在发展中国家,如今中国、印度每年智能手机都是以几千万的速度在增长,而非洲国家也会成为新兴市场。未来将会有30亿新网民加入到互联网,这蕴含着巨大的应用需求,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创造力。斯密特还畅想了一系列新兴应用,比如无人驾驶汽车、穿戴式设备等。 报告结束后留了半个多小时提问,大家非常踊跃。有人问Google是否能帮助设立诺贝尔计算奖,Google的数字货币计划是什么,未来该如何学习快速发展的技术,互联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区别,Google在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还有人提问请斯密特给本科生一些建议…… 我也起身问了一个关于Google X实验室的问题,并开玩笑式的问怎么才能进Google X实验室。斯密特说,有人泄露Google X的信息,Google X实验室细节仍然是机密,所以他可以透露无人驾驶汽车项目,但不能再说更多其他的项目,不过请想象一下Google X的研究人员正在整合计算机科学、硬件和新设备,那也许会对Google X有一些感觉。事实上,Google X确实很秘密,存在好多年而不为人所知,即使是Google员工。直到2011年11月纽约时报泄露有关信息,外界才得以了解。Google X项目都是非常激进,比如无人驾驶车、Google 眼镜、机器人巡逻队、甚至太空电梯。上期CCCF刊登的CACM译文《谷歌的混合研究方法》(Google’s Hybrid Approach to Research)中提到工程与研究并重的混合研究模式会更倾向于低风险的短期项目,而专注长远影响的Google X实验室则是对混合模式的补充。 斯密特提到的很多观点和我最近读的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的《Abundance:The Future Is Better Than You Think》一书中很多观点一致。事实上,斯密特和戴曼迪斯本来就是私交很好的朋友,他们甚至最近和Google的创始人佩奇(Larry Page)、《阿凡达》导演卡梅隆(James Cameron)一起宣布创办了Planetary Resources公司,目标是太空采矿! 斯密特和戴曼迪斯对未来的判定并不是凭空臆想。如果跳出某项具体技术,从更广阔的时空来观察技术本身的发展,就会发现技术发展也有规律。比如,笔者之前在CCCF上刊登的《谁推动信息产业发展》文章中引用了美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分析了19个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史,从而得出基础研究与产业化互动的一些规律。而《Abundance》一书给读者呈现了另一条有趣的规律——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都是指数发展型技术(Exponential Technologies)。 在科技史上有很多成功利用这条规律预测未来的例子。例如1953年美国空军分析了从1911年飞机发明到1953年之间飞机加速技术发展曲线,发现飞行器发动机的加速度增长是指数发展的,并预测1970年左右人类便能登上月球。这个判断是在1953年做出来的,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最乐观的估计也认为登上月球至少还需要50年(2000年左右)。 而摩尔定律是计算机领域都熟知的另一个例子。1965年摩尔(Godern Moore)在一篇文章中用1959年到1965年的5个点画出了一条直线,并成功预测未来10年(到1975年)半导体技术的发展趋势,即单个芯片晶体管数目将每12个月翻一番(后来修正为每18个月)。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摩尔定律在过去的50年里都有效,并还会持续到至少2020年。 从技术层面上去判断一项技术是否为指数型技术需要极远的眼界和很深的造诣,往往只有摩尔这样的大师才能做到。我的一个观点是,技术的成本也许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判断依据,即在相同的性能下价格是否在不断下降,或在相同的价格下性能是否在不断提高?当然技术的潜力还依赖于市场饱和度。所以,综合技术成本和市场饱和度两方面的因素来看,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确实还有很大的潜力,尤其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5. 结语 | |
华盛顿不相信眼泪 — 从华为中兴新败于美国之役说起
作者 陈怀临 | 2012-10-20 21:43 | 类型 弯曲推荐 | 52条用户评论 »
|
华盛顿不相信眼泪 — 从华为中兴新败于美国之役说起
海客( @追梦海客 )
2012年10月
1987年任正非集资人民币两万元创立了华为公司,短短二十五年间,华为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乃至电信业的心脏地带欧洲攻城略地,迅速崛起为仅次于爱立信的世界第二大电信设备生产商。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华为数次尝试拓展业务,始终不得其门而入。近年来华为发起数次对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并购案,均已失败告终。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资本(Bain Capital)试图以22亿美元收购美国网络设备制造商3Com公司16.5%的股份,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该交易启动国家安全调查,不久后以3com公司持有大量军事合同为由提出反对意见,华为被迫放弃该收购案。2010年8月,美国移动电话运营商斯普林特公司(Sprint-Nextel)发起网络升级的招标,华为和中兴希望参与其中。虽然华为提供的解决方案报价大幅低于竞争对手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和三星的报价,却遭到美国参议员的横加阻挠。他们致信总统奥巴马和财长盖特纳,要求对华为公司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进行彻查,时任商务部长的骆家辉也要求斯普林特拒绝华为与中兴的投标,最终提出最低报价的华为和中兴无缘这个50亿美元的网络大单。2011年2月,华为卷土重来,试图以200万美元收购濒临破产的美国IT初创企业三叶系统公司(3Leaf Systems)的资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再次披挂上阵,要求剥离合同规定的专利资产,该收购计划随即流产。在收购三叶公司失败后的同一个月,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华为美国公司董事长胡侯崑发表了一封针对美国市场的公开信[1],信中希望美国公开调查华为公司,以期澄清与纠正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对华为公司的偏见。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IC)遂展开对华为是否危害国家安全的初步调查,2011年底开始正式展开调查并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对中兴通讯公司的调查。今年9月13日,情报委员会就华为、中兴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举行公开听证会。华为高级副总裁丁少华与中兴高级副总裁朱进云出席听证会[2]。10月8日,该委员会对华为和中兴通讯为期一年的调查结果报告终于出笼。在对外公布的的非机密部分,给出了调查结论:“华为和中兴通讯公司提供通信设备给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相关风险,可能会消弱或危害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该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阻止这两家公司对美国公司的收购行动,避免使用这两家公司的设备以及进行其他形式的合作,美国企业也应寻找可替代华为与中兴通讯的电信设备供应商[3]。
在接受情报委员会近一年的调查过程中,身为全球第二与第五大电信设备生产商的华为与中兴公司,为了能够进入美国市场,极力放低身段,委屈求全,尽量配合情报委员会提出的各种要求,大有哀兵求胜之态。华为在去年12月正式向情报特别委员会汇报了相关情况之后,又在今年2月23日在深圳华为总部接待他们参观考察。今年5月23日,公司罕见地安排该委员会在香港一个私人俱乐部与总裁任正非当面会谈,试图消解委员会对这位公司领导人的神秘印象。6月份收到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清单后,华为公司按约定做了回复。在9月13日的听证会上,华为与中兴公司的高管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小组面前不可谓不配合,不可谓不低姿态。在媒体所称的“在长达3小时的激辩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位高管的动情陈述,小心回答,竭力试图说服美国议员。两公司进入美国市场为美国人民服务的诚意,足可教日月动容。对美国议员的提出的种种要求,如公司党组构成,与政府关系,经营状况,甚至一些涉及公司机密的合约细节,都口头答应将书面提供。华为中兴两位高管表现的前所未有的诚意,换来的只是问询者怀疑的目光。委员会最终出台的报告中称,“中国具有恶意使用通信公司的途径、机会和动机。”背负了中国原罪的华为中兴高管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战斗。无论如何努力,埋藏在议员先生们心中对两家公司根深蒂固的怀疑,像西西弗斯的巨石一般一次又一次地滚回到他们面前。
在情报委员会对华为中兴公司提出的诸多指控中,其中一条是担心中国政府要求华为与中兴在其制造的设备中植入恶意程序,以在需要的时候对美国进行网络战争。应当说美国的担心并非出于凭空想象,因为他们本身不但精于此道,更是这种极具破坏力的网络战的鼻祖。1982年6月,美国中情局为了攻击连接西伯利亚和欧洲市场的苏联天然气管道,布下了所谓的“逻辑炸弹病毒”陷阱。他们在一套从加拿大购买的软件中加入了恶意程序,并通过这个软件进入苏联管道控制系统,引发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大爆炸。美国空军估计爆炸有3000吨当量,相当于一次小型核爆炸。那次攻击严重打击了当时的苏联经济。中情局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的托马斯·里德(Thomas Reed)在2004年出版的《在深渊:一名知情者讲述的冷战史》一书中披露了这个事件。另一起著名事件是小布什当政时期启动了代号为“奥运会”的网络战计划。该计划由美国与以色列专家秘密联合研制了专为袭击离心机而设计的蠕虫病毒“震网”(Stuxnet)。2010年夏季,“震网”蠕虫病毒在伊朗纳坦兹核电站潜伏了一年之后一波又一波地爆发,病毒突然改变了离心机中的发动机转速,摧毁了离心机的运转能力并对其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那次连环攻击造成伊朗近1000台离心机瘫痪,以色列评估攻击造成伊朗制造核弹的计划至少推迟了两年。若不是该病毒在发起攻击前的6月意外脱离伊朗纳坦兹核电站,散播到全世界的互联网系统,世人也许直到现在还要蒙在鼓里。根据赛门铁克公司的一份报告,到2010年9月底为止,“震网”病毒在世界范围内感染了10万台主机,其中有6万台位于伊朗。有句话说自己是贼,看别的人也都像是贼。美国作为网络战的老祖宗,自然对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前景感到恐惧,而华为中兴公司生产的网络设备,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情报人心目中潜在的“特洛伊木马”。
在听证会上,美国议员对华为与中兴公司内部的党组问题不断发难,同时还质疑他们与中国当局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早在去年11月,美国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AEI)发表了一份由该所高级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撰写了一份题为《电信与华为难题: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的报告[4]。这份报告讨论了美国应该如何权衡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与安全风险,并在概述部分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建议,其中多项建议被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10月8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所采纳。今年3月22日,企业研究就这份报告举办了一次专题讲座,邀请了华为美国公司副总裁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报告撰写人克劳德.巴菲尔德、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乔治城大学的西奥多•莫兰(Theodore Moran)、和2049项目研究所的马克•斯多克斯(Mark Stokes)等多名学者参加[5]。巴菲尔德在讲座上援引著名智库兰德公司2005年的一份研究称:“兰德公司的研究提出中国的‘数码三角’,一方是人民解放军,一方是研究机构,第三方则是国营或私有企业,这三方有着紧密关联,有着某种协同关系。而这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华为在1999年之后这十年的发展,就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很明显的,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操纵了电信产业。”
美国之音在报道这次讲座的文章《美专家:华为难撇共党原罪》中援引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剑道的话说,“没错,我认为华为背负了原罪。”他说,受到中国政府扶植的中国电信企业,背负着共产党的原罪以及中国政府的战略考量,因此不适宜对此两家公司开放美国市场。事实上,他给美国政府的建议是,彻底封杀华为与中兴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他的这个建议显然也被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所采纳。 对于被问及至关重要的中国国家安全法第十一条,即“国家安全机关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可以查验组织和个人电子通信工具、器材等设备、设施。”[6],如果中国政府援引该法律,要求获得访问客户所用设备的权限,公司会否拒绝时,华为与中兴的高管们先是称不清楚有这条法律,或没有相关知识,然后竟然罔顾公司母国法律,称如果遇到以上情况,公司考虑到他国法律和为了保护客户,将会对政府说不。话都说到这份上,美国的议员先生们满意了吗?来看看提问的众议员亚当•希夫听到他们的回答后是怎么说的吧:
“先生们,我感谢你们的回答,但我认为你们在你们的中国和美国顾问的知会和代表下,已经到了对这条直接作用于你们所从事行业的法律没法不熟悉的程度。我想如果真有这样一件案子,公司对来自共产党或政府的要求说不,而当你们向法庭寻求保护你们的决定时,你们也将能够认识到这条法律。我感谢你们美好的意向,但你们运营在一个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中国法律系统内,在这个系统内你们还无法向法律寻求安全保障,以及向中国政府说不。你们生活在一个你们的政府从事着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行为的环境里,这是你们和其他中国企业所正在背负的负担。我感谢你们试图发展你们的公司并以一种合法的方式运营,但中国法律白纸黑字地告诉你们,当政府要求访问你们的设备时,你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方便。我看不出你们有任何机会能在现有中国法律系统内挑战这种现状。”
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Game Over!
应该说,华为中兴遭到美国立法机构的强力封杀,美国议员们只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上世纪苏联垮台后,一家独大的美国不甘寂寞,迅速为自己找到了下一个对手–中国。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从战略合作伙伴,到战略竞争者,到佐利克提出的利益相关者,名称变来变去,实施起来内容只有一个:接触和围堵。当美国需要中国时,接触就多一些;而大部分情况下,围堵占了上风。作为世界独霸的美国,看着身后紧追不舍得中国,第一反应也不可避免地是围堵和限制。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使两国存在不可消弭的怀疑情绪。中国近十年来迅速超越工业国家中的意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成为国民总产值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单一国家经济体,工业产出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国。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多是农产品,进口多为高科技产品,以至于经济学家说,从贸易成分看,和中国比起来,美国更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华为的成长就是中国实力成长的一个缩影。华为在二十余年间,由一家汲汲无名的小公司,通过多年的辛勤耕耘,一步步超越了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和摩托罗拉等业内巨擘,去年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生产商。今年上半年营收更首度超越领头羊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生产商。今天的华为公司,拥有与西方媲美的技术,有着近14万年轻的员工,客户遍及全球140个国家,俨然成为一个营收超过300亿美元的企业帝国。与华为中兴不断的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其他主要电信网络生产商却在竞争的压力下遭遇危机,盈利下降,不断裁员,诺基亚-西门子和阿尔卡特-朗讯不得不靠合并以图提高竞争力,摩托罗拉卖掉了网络部门,而曾经占领加拿大股市市值三分之一的北电网络,干脆关门大吉。奥巴马政府在金融危机后,为了解决美国高居不下的失业率问题,提出了复兴美国制造业的口号。电信网络设备制造业和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服务业,能为美国提供大量工作机会,又涉及敏感技术和国家安全,中国电信企业在这一领域遭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壁垒成为必然。凭借美国公众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不信任,美国政府、立法机构可以毫无政治风险地封杀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的业务。在这样的美国内政环境下,华为中兴再如何解释与释放诚意也只能是徒劳。
华为公司在创业初期曾经在本国也很难拉到顾客,然而任正非明智地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不避条件差,利润薄的项目,靠着华为人在国内和亚非拉国家辛勤耕耘,逐步为其产品和服务赢得了声誉,华为可以说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电信科技发达的欧洲市场,华为也获得已宣布的4G电信网络过半数业务,成为高手云集的欧洲电信业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在重要的国家宽带网络(NBN)建设项目中,华为中标8个国家的网络建设,成为全球获此类合同最多的供应商。应当看到,新兴市场的利润虽然远不及欧美市场,然而中国企业在那里遇到的政治阻力一般较小,尤其是在经济增速很高的非洲大陆,华为与中兴有着西方公司不可比拟的成本比较优势,获得这些国家的合同远较西方国家容易。对于华为和中兴公司而言,新兴国家市场就是美国人常说的“低垂的果实”(low hanging fruit)。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也有着更广阔的市场前景。近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经济上飞速发展,居民收入的增长创造了大量中产阶级,以及新增的购买力。随着经济后起之秀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的市场等待开拓。由于手机拥有量超过人口总数的国家越来越多,从长远看,有着更大人口基数的发展中国家比西方国家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不难预见,发展中国家才是中国企业未来盈利的增长点。继续在发展中国家开拓和深耕,华为和中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此时华为中兴贸然放弃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操之过急地强攻美国市场这个最坚固的堡垒,可谓是战略方向上的根本错误。而华为在舆论准备和游说工作都不足的情况下贸然要求美国对自身进行调查,无疑是引火上身,失败在所难免。
华为中兴在美国的失败,后果可能是连锁反应式的。澳大利亚之前已经明确禁止华为参与该国国家网络(NBN)建设。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向来在政策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如果委员会所建议的限制中国电信公司参与美国电信市场项目与并购美国公司的立法获得通过,加拿大也很有可能修改本国法律使之与美国法律保持一致。华为公司引以为豪的在加拿大刚刚起步的业务,将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挫折。事实上,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一出炉,加拿大政府已经暗示,该国一个计划中的政府通讯网络项目将会因为安全风险的考量,排除华为的参与。渥太华方面引入了一个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允许其在不违反国际贸易义务的前提下,区别性对待某些对政府网络系统构成潜在隐患的企业。在自由贸易思想根深蒂固的英国市场,本来华为已经获得了良好开端,现在也无法排除欧盟在美国的示范作用下,重新启动对华为中兴的安全调查,在未来的竞标中排除中国企业的参与。
既然已经遭到美国的重手封杀,华为中兴是否就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了呢?本周传出华为老总任正非在内部讲话时称,决定放弃之前“韬光养晦”的战略,改为与美国企业正面竞争。这样的豪言壮语,虽然能激励人心,却实在看不出如何实现。首先,在目前的形势下,华为公司不仅拓展不了在美国市场的业务,恐怕连保持已有成果都有困难,可以说在美国市场能否生存下去都已经成疑,华为如何与美国企业“正面竞争”?而在美国市场以外的大多数国家(不含印度),华为依靠价格优势,早已在“正面竞争”中将美国公司打得节节败退,自然也无所谓放弃“韬光养晦”的战略。企业的本分,应该是广交朋友,广开财路,从善如流,和气生财。坏蛋的角色,还是应该留给政府和立法机构来扮演比较合适。既然美国动用了国家机器封杀中国的高科技皇冠企业,华为中兴靠自身的能力已经无力抵挡,英雄救美的大戏,必须由中国政府和立法机构来完成。经过多年的韬光养晦和休养生息,中国早已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幼雏,而是已经成长为“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了。面对美国在经济上的强势挑战,中国完全可以做一个称职的对手,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
首先,如果美国政府按照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建议封杀中国电信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已经构成对中国企业的国别歧视,中国商务部应当理所当然地到世界贸易组织控告美国。根据世贸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在获得裁决之前名正言顺地对美国产品启动等量贸易报复。由于华为中兴公司在其他经济体所占市场份额巨大,估算出来的在美国市场遭到的损失必然也十分巨大。中国政府不妨制定多个层次的贸易报复清单,酌情对美国的多个领域的美国产品加以制裁。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电信业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无法奏效,可以考虑对美国选民十分敏感的农产品发起报复。进行制裁的同时,应当声明中国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的自卫行动,希望与美国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只有美国政府回到谈判桌前,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的市场准入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华为中兴在美国市场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的先进性,也不在于产品的价格,甚至不在于产品的营销,关键在于公司形象的宣传,能否说服美国的民众和政客接受自己,是华为与中兴在美国存在的基础。要想在美国这个中国以外最重要的海外市场获得成功,并没有什么捷径而言。如果当初华为将美国公司副总裁威廉•普拉默提拔到美国公司总裁的职务,放手让他在美国进行长期广泛的公关,努力提高公司在美国社会和政界的接受度,华为或可有一线希望逐渐打开美国市场。然而经过这次挫折,华为中兴将遭到美国立法机构和政府的联手封杀,美国网络市场的大门已经基本关闭。华为现在所能做的,首先是尽量说服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保持与自己的合作。在安全检查的程序上形成一套公开可信的措施。在保住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国重要盟友市场的基础上,用行之有效的安全解决方案证明美国封杀中国企业的理由不能成立。在美国市场,华为中兴暂时只有忍耐,耐心等待时机的来临。如果将来经过中美两国的博弈华为中兴能够留在美国市场,今后他们在美国所能做的,也许只能低调培养市场,努力拓展不那么敏感但有前景广阔的的终端市场,在产品线上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美国多进行低调有效的公关活动,逐渐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以期在未来的网络市场分享利润。
华为与中兴已经发展为国际性大公司,海外营收占了大部分,华为目前的收入大约70%来自海外市场。可以预计未来,两家公司海外营收所占比例仍将保持在高位。两家公司专利申请在国内为前两名,在国际上也是名列前茅,保护知识产权关系到未来两家高科技公司自身的利益。华为与中兴要想在未来获得更大的成功,必须在经营方式,法律承担,公司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完成从初创公司到国际知名大公司的转型。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始终怀疑中国政府持有华为股份或者是华为的实际控制者,他们对任正非的背景尤为关心。由于美国国会的这次调查,华为公司在发布2011年年报的同时,首次详细披露了其董事会、监事会、三大业务集团的管理层名单,以及其专业委员会名单。在1名董事长、4名副董事长、和常务董事和董事各4名的高层管理成员名单中,任正非仅排在副董事长中的最后1名。然而在听证会上,华为副总裁丁少华向美国议员承认,任正非在华为公司拥有特殊的地位,即虽然他名义上只是公司副董事长的最后一名,却对公司所有决策以及股东大会的决议拥有否决权。试问,一个排名垫底的副董事,为何能够拥有其他更高级管理人员都没有的权利?这样的安排,如何能够让公众相信,华为公司是在进行正常的公司管理?华为公司要想将来在美国和西方法制高度健全的国家获得成功,正如情报委员会报告中所说的,必须变得更加透明,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重视所在国的法律义务,并对正常的公众媒体和管理机构所提出的问询反应更加积极迅速。而美国法律要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司必须成为上市公司,华为公司未来在国内与海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真正的公众公司,是唯一的选择。
| |
EMC中国研究院:存储网络虚拟化——曾经的北大荒,还是撒哈拉沙漠?
作者 陈怀临 | 2012-08-10 17:08 | 类型 专题分析, 弯曲推荐, 科技普及 | 2条用户评论 »
|
网络虚拟化如今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各大厂商都在忙着争抢这块蛋糕。涉及的技术包括包括网卡的虚拟化(Emulation, I/O pass-through, SR-IOV), 网络的虚拟接入技术(VN-Tag/VEPA),覆盖网络交换(VXLAN/NVGRE),以及软件定义的网络(SDN/OpenFlow)等等。具体的介绍大家可以参考EMC中国研究院之前的一篇博客——“网络虚拟化-正在进行的网络变革”,其中对网络虚拟化的现状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所说的网络其实是狭义的数据通讯网络,包括通常所说的局域网(LAN)和广域网(WAN/Internet),所采用的协议有以太网(Ethernet,二层)和英特网(IP,三层)协议等等。然而在企业级的数据中心(或云计算的数据中心)里还有一类重要的网络,那就是存储网络(StorageNetwork),占统治地位就是基于FC技术的存储域网络(SAN)。存储网络的虚拟化似乎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虽然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工作开展,但总体上还是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存储网络虚拟化的前景如何,到底是未经开垦的处女地(曾经的北大荒),还是不毛之地(撒哈拉沙漠)? 存储网络简介 存储网络通常也被称作存储域网络(StorageArea Network, SAN),是为块级别(blocklevel)数据存储提供统一访问的专用网络。其中的支撑技术就是光纤通道(FibreChannel,FC)技术。FC不是搭建存储网络的唯一选择,但却是业界应用中占统治地位的技术。FC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含义:(1)传输媒介,能够提供长距离、高速、低延迟、低出错率的传输,以及通过硬件(HBA)实现传输协议(注:在这里光纤(fiber-optic)同样也不是必须的);(2)传输协议(FibreChannel Protocol,FCP),一个五层的网络协议栈(FC-0到FC-4,大家可以类比一下ISO的七层协议栈)。关于FCP这里只提一下其中比较重要的两层:(1)FC-2是数据传输层,可以在这里进行数据帧的流量控制(flowcontrol);(2)FC-4是上层协议映射层,实现对应用层协议(SCSI,IP等)的映射。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了问题,这里为什么会有IP协议呢?这里有个小插曲, FC协议最初是作为局域网(LAN)的主干网(backbone)技术设计的,用以代替百兆以太网(Ethernet)。当然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千兆和万兆以太网技术完胜。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LAN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么基于光纤通道技术的SAN与其相较到底有和异同呢?图1是数据中心中LAN和SAN的一个简化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在SAN的构建中同样也采用了交换技术(Switching)。其实两者之间大多数的概念都是可以类比的,这里只提两个关键的不同点。其一, LAN是一个全联通的网络,任何两个节点(主机)之间都可能存在通讯;SAN从图论的角度来说是一个二分图(组1:主机,组2:存储系统),即组内部不存在任何通讯,所有的通讯都发生在组间。其二,LAN是一个尽力服务(best-effort)的网络,拥塞丢包都可能出现,可靠的数据传输依赖于上层协议(如TCP);而SAN则提供非常可靠的数据传输,上层协议(SCSI)对丢包的容忍性要差很多。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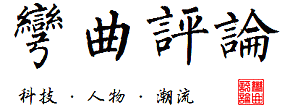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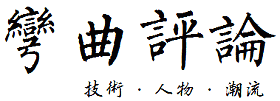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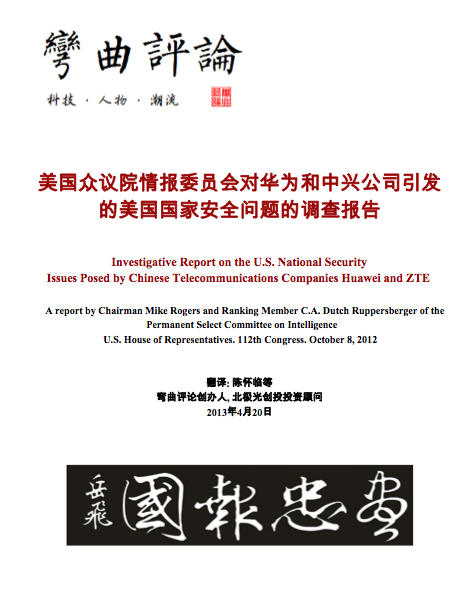

 (12个打分, 平均:4.67 / 5)
(12个打分, 平均:4.67 / 5)